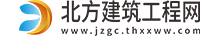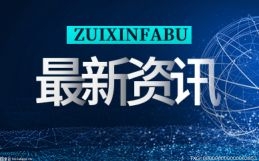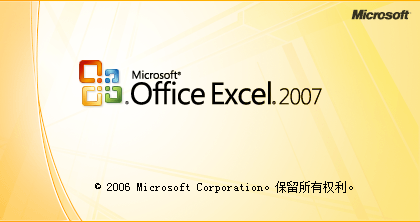晚潮|老井
潮新闻客户端 沈若尘
一
 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我把它称之为老井,是因为新中国成立初年我家迁居到这里来的时候,它已存在了。而且是一口被青石板盖住,压在废弃的瓦砾碎砖下面的井。老井的以往岁月已经无从知晓。
一个陈旧宽大的朝东大台门,是我们在上虞古县城的新居。光从台门的宽大气派看,台门里边曾经的主人,自然也是家财丰厚、丁旺德重之家。大门内是一个一丈余宽三丈余长的天井。天井地面一改城里大户人家以青石板铺地的做派,精选深山大溪的浑圆卵石密实铺排,又以黑色卵石编排出来的双钱图案镶嵌其中;正对着双钱图案上方的是一块长约八尺,宽二尺的平整的青灰色条石台阶,白晃晃地暴晒在火辣辣的阳光下,在杂草丛生的卵石地坪中,显得特别抢眼。走上一级台阶,是长短不一,沿着屋基四周整齐排列的青条石,看样子是房屋残存的基石。还有几只腰鼓形的柱础石磉礅,散落在废墟的杂草藤蔓乱麻当中,显得沧桑晦暗,凌乱无序。
在老台门里,不见春花绽放,也没有吐蕊海棠,满眼尽是被岁月熏蒸而苍老皲裂的墙皮,被风雨蚕食而倾颓的黑沉沉瓦檐,让昨日天上的明月,成了今日地角的沟渠。
这里,是古县城闹市的核心。家父遴选了好几处住宅以后终于看中的独门独院,百年老宅。
被百年风雨潦倒的老宅,得遇新主,只希望从今后不再沉沦,而是再度倔强,赢取繁华依旧。
这一处房屋的选择,家里家外自然也有不少的非议。很多坊间传闻的包括易经八卦在内的神鬼风水,房屋和房屋主人的种种传闻,希望动摇家父放弃这里,另做选择。
这样看来,并非每一个旧事物的存在都没有意义,总会有人用他的执着在守护这种看似不起眼的,或者即将消失成为时代记忆的东西。家父就是。
百年之前,这座略显气派的宅邸因何毁于一旦,为什么家道中落到不可收拾?仅凭口耳相传的几句闲言碎语,全然不能作真。家父是个唯物论者,现实主义思想在他的头脑中稳居上风。觉得这房屋的前生前世与他无关。家父在意的是,构架结实的侧屋用作自己一家的住房和商店的库房,非常的合适;废墟上面空旷的黑土地可以用来栽种蔬菜作物。稍稍勤快一点,一家人每天的蔬菜就可以自给自足了。何妨又是在一个特殊的物资匮乏的年代。在那个年代里购房置业,他觉得这价格很实在,很受用。
二
发现老井是一笔意外的收获。
废墟四周种上了蓖麻、熟地、苎麻、苋菜以后,需要清理地基中间的瓦砾碎砖。这天,家父在靠近西侧屋的地基整地。一锄头挖下去,“咚”地一下被震得双手发麻,下面是一块大石头?他扒去表面的软土层,发现是一块硕大的青石板。家父心里好一阵紧张和激动。
这石板下面会是什么东西?好奇心驱使,他屈身趴在石板上面敲击听声,除了中间有“空空空”的回声之外,听不出其他声音来。他觉得这下面肯定是一个地洞之类的暗窖。难道说,这房屋早先的主人曾在这里藏过什么东西?难道说,这下面还会设有机关暗道?
怕万一有什么情况,到时候自己说不清楚,得有人在一旁做个证,因此,家父不敢贸然撬动那块石板。他快步跑出弄堂,在街上找了几个相熟的朋友来帮忙。听家父粗粗一说,一起来帮忙的几个人倒是热闹了:
“沈先生,你要发财啦!地下肯定埋了不少金元宝银洋钿。”
“没有这么好的事情的。有金银珠宝埋在地下,他们的子孙自己先要搜一搜来!不会傻到房子卖掉之前不做手脚。”
“当心点,长期盖着的洞里可能有蛇毒邪气!”
……
但是他们根本想不到,移开那块石板以后,发现石板下面只不过是一口平常不过的小小水井。
一潭死水,安静无澜。拿来手电筒,强光直照井底,井底一览无物。黑黢黢的井筒里唯一可见的,只有那片倒映在水里的井口般大小的天空。
地处江南水乡的上虞古县城,1970年以前,居民还没有用上自来水。城南城北有百楼、萝岩两山夹持,东西向四十里运河已经贯通。自古以来烧茶煮饭积雨水,生活用水在河湖,天旱地干找井、泉水。用井水来补充日常生活用水的人家,不在少数。缘于古县城设治一千多年以来一直困扰人们的用水之难。1934年入夏以后,古镇遭遇罕见大旱,旅沪帮佣的范氏老太以一己之力,慷慨捐建八口新款自由方井,分布在古镇五城门门内的县前、学宫前、东正小学前、南街文武庙前、北门弄、黄泥道地、西南门等镇内各个地方,以缓解城里百姓的水荒。范氏老太,乡里人称“八太娘”的大义慈善之举,一直以来为古县城的人们热烈称颂,感动着一代又一代的家乡人。
在古县城,一般人家,家里总要备两只水缸,灶头水缸和天落水缸(雨水缸)。那水井恰好似一只公用的大水缸,多数是随用随取的。古镇里的人习惯地认为天落水是无根水,日常用它泡茶是最好的,所以每逢下雨,千方百计要积满一缸备用;流经街河的运河水,只要曹娥江没有咸潮进入,上游没有黄泥大水下来,经过一夜的沉淀自净,河水清澈见底。因此,每天大清早家家户户从街河里挑水,是古镇一道颇为有趣的景观;井水,具有恒温的特点,冬暖夏凉,水质清冽纯净。在古镇行走,常常可见一些人在井边洗洗刷刷地忙不停手,特别在冬天,一丝丝的地热蒸气缓缓地从井口往上冒出来的时候,即使畏冷怕冻的人,也可以无所畏惧地出手去洗刷洗涤。
“雨馀古井生秋草,叶尽疏林见夕阳。”
废墟的杂草藤蔓乱麻当中发现的这一口私家小井,很快融入到了我家的日常生活当中。
这口井并不大,深不足两米,呈上小下大的葫芦形。内壁最大的直径也就是一米多一点,井壁采用青砖错缝堆砌,井口只有50厘米左右。一口私家井,就好像是埋在地下的一只超级大水缸。因为家里突然有了一口水井,从此,也就多了许多与水井有关的开心事。
三
不出家门,就有一口水井可用,最开心的人要数我家老祖母。
本来每天天一亮,她就要拿两只小水桶,去后井拎两桶井水的,现在不用去了。祖母是清光绪二十一年生的人,一双“晚清小脚”比真正的三寸金莲实在也大不了多少。以鲁迅先生笔下的“豆腐西施”来比较,称为“圆规”是一般无二了。每天要祖母扭着一双小脚,提着两个小水桶,袅袅婷婷地步行到三百米开外的后井,打两桶井水回来,这个任务的艰巨性可想而知。虽然现在祖母不用再到后井去打水了,不过祖母仍然有她的考量与要求,她说:“最好这口井的水全都换一次,用起来也放心一点。”
家父赞同,说他去找朋友想办法,尽量把存水换掉。那时候,丰惠镇上还没有开通居民用电,没有抽水设备,要换一井水,谈何容易。
后来,母亲从医生那里得来经验,说用漂白粉可以杀菌消毒,明矾可以澄清水质,一试,果然有效果。这事才平静下来。
一开始用这口井水时,谨小慎微,井水只用来拖拖地板,洗洗桌椅板凳,再给菜地浇浇水。用顺手了,渐渐地胆子也大了。一步步地洗衣、淘米、洗菜觉得也没问题了。
本来,祖母每天一早提着两个水桶去后井提水的情景,早已如同摄录影像一样定格在左邻右舍的脑子里了。突然之间不见祖母的身影,不少人好奇地打听其中的因果,祖母大方地告诉他们:我们家里现在有一口井了,你们如果需要,来我家打水用水好了。
懂得利用这口井的人,要数家父了。
生活在东三省的人们,利用天寒地冻的自然条件,把不易在常温下保存的食物,存储在雪地里,地窖中,随时取用,可保较长时间不变质,充分享用了自然天气资源的福利。家父正是看上了这一点,使这口小水井成了我家的一只“大冰箱”。
家父有一个嗜好,每天中晚两顿饭时,总要喝点小酒,量不大,但是不能断。盛夏天,高温酷暑,天干地燥。没有冰镇的条件,把啤酒整瓶浸入井水里面,一两个小时以后再喝,那凉簌簌的感觉比冰镇的更温柔,更和顺。看到父亲悠然舒畅地喝下那一口冰镇啤酒的舒爽样,馋得不得了。可惜那时候没有饮料,最好的就是汽水、果子露。不然我们小孩也是可以分享到这种甜蜜的。
因为有了一口井,为充分利用水井的恒温功能,家父做了许多相应的工具。用一根根绳子装上钩子,钩挂在井圈沿上面,这样,井中取物非常方便了。沉入水中,多数用不同网眼的网袋装载,偶尔也有一些时菜,怕高温,就用篮子挂在井下水面上。
夏天,每天傍晚吃一只井水冰镇的西瓜,是我家兄妹最大的期待。每一天的乘凉开始之前,几个小孩心心念念的,必定是沉在井里的西瓜。
“转载请注明出处”
标签:
X 关闭
X 关闭